萧红情史:私奔、同居、弃子,讲述了“性解放”下的悲凉人生
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钟,萧红在香港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的人世。
临死之前,萧红曾经说过:
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”
因为是女孩,萧红从生下来就受到了父母亲的冷遇。
萧红的父亲是过继子,所以特别期望头胎是男孩。
同时萧红的降生,也给重男轻女的母亲不小的打击与压力。
在父母处,萧红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与关爱。
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长,他从不苟言笑,更别说对幼小的萧红有任何温暖的举动了。
有一次,祖母过世,淘气的萧红头顶了一个大缸盖,踉踉跄跄地走到父亲面前。
父亲看到非常恼火,一脚就将她踢到地上。
母亲呢,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又连生了三个男孩子。
加之祖母过世,家务缠身。她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萧红。
萧红八岁时,母亲因病去世。
所以,萧红对母亲的印象非常淡薄。
童年的经历给萧红留下了深深的创伤,让她一辈子都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。
而后她的三段失败的恋情又将她推入深渊。
萧红的悲剧其实就是那个时代女性悲剧的缩影。
她出生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,生长于封建男权之下。长大后又接受了新式的教育,成为了一个勇敢自由的女性主义者。
这种时间与文化的割裂,导致了萧红的悲剧衍生。
而她与王恩甲、萧军与端木蕻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,更是造就一个伟大的新文化作家,与一个漂泊孤苦的女人。

萧红十三岁的时候就与汪恩甲定了婚约。
与汪恩甲见过几次面后,萧红对他的印象还不错。
但是,后来听说汪恩甲抽大烟,萧红对他的印象就一落千丈,于是她就萌生了退婚的念头。
单方面解除婚姻,在当时来说,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丑闻。
萧红的父亲以断绝她经济来源来逼她就范。

萧红是一个骨子里很倔强的女人,越是硬来越适得其反。
她和她的一个表哥私逃到了哈尔滨。
萧红追求独立自主的行为,将他的父亲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政府以他教女无方为名,降了他的职位。
汪家人也对她恨之入骨,将她归为行为不检点的女子一列。
为了反抗旧式家庭追求婚姻自主的举动,在旁人看来就成了大逆不道的荡妇行为。
表哥也受到了牵连,被家里断了经济,最后不得不向家里妥协。
萧红这时候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,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。
有一天夜里,她独自在街上游荡,看到青楼里昏黄的灯光,竟生发了对低贱卖笑女的艳羡之情——至少她们还有一个安身之所。
就在这个时候,身为小学教员的汪恩甲找到了她。
萧红与汪恩甲就住到了东兴顺旅馆。
她与汪恩甲的这段同居历史,在萧红的任何作品里都不见踪影。
汪恩甲这个人,在她的作品里也察无痕迹。
由此可见,汪恩甲以及与他的一段往事,都是萧红极力要抹去的一段黑历史。
选择与汪恩甲同居,实则是萧红在艰难处境下不得已而为之。
她不能理解,一个父亲对亲生女儿冷漠到如此地步。
父亲的不闻不问置她于生存的绝境,压迫着她使她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初衷的决定。
汪家人不能接受汪恩甲与萧红同居,由汪家大哥出面,强行带回了汪恩甲。
萧红一气之下,状告汪家人背弃盟约,逼人休妻。
这场官司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。
萧红以为凭借汪恩甲对自己的爱,完全可以胜诉。
只要胜诉,不仅能挽回颜面,还能得到家人的谅解,夺回属于自己那一份嫁妆。
就在萧红踌躇满志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。
汪恩甲当庭反戈,主动提出要和萧红解除婚约。
这下,萧红成了老家最大的笑话。父亲一气之下将萧红从族谱除名。
萧红灰溜溜地回到东兴顺旅馆,汪恩甲随后也赶了过来。
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哄得萧红继续与他同居,并且还怀了孕。
就在孕期的第五个月,汪恩甲出走了,从此再也没有出现,连带整个汪家人也全部人间蒸发。
这一年,萧红只有二十岁。
这时,她面临的困境不再只是挨饿受冻,还要承担做母亲的责任,和汪恩甲欠下旅馆的六百块房费。

因为是女人,她从小被忽视;因为是女人,她无处谋生,只能依靠家庭与男人的救济。
而当家庭和男人都抛弃她的时候,能够救她只有命运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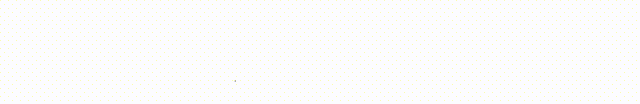
命运将萧军送到了萧红面前。
萧红欠了钱,旅馆老板将她赶到杂物房,并威胁她要将她卖到妓馆去。
自尊心强的萧红不愿向父亲求救,如果她向家里求救,要么是回家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家庭妇女,要么是被置之不理,再次感受原生家庭加之于身的刻骨冰凉。
不愿遭人白眼的萧红,决定要自己的力量一搏。
她写信到报馆求救。
报馆委派萧军去探明情况,这就有两萧的第一次会面。
第一次见面,萧军就为萧红的才情所折服。
他看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女人,顿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保护欲。
尽管此时他也自身难保,朝不保夕。
第二天,萧军又敲开了萧红的房门。两人发生了关系,开始了长达6年漫长的情感纠葛。
两萧恋情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
在恶劣的处境里,萧红迫不及待地需要有人能救她出水活,萧军就在这个时候充当了救世主地角色。
萧红就像一个溺水者,迫切地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女性骨子里对爱情充满了浪漫的幻想,汪恩甲的消失,让萧红不再相信软弱的书生。
萧军尚武,强壮有力,与人搏斗,歹人不敢近身。
但是,萧军还是固守着旧社会的那一套传统——人不风流枉少年。
萧红则是爱情至上者,她将萧军视为唯一。
但是,在萧军看来,萧红只是他若干情人中的一个。
他向萧红坦言自己的爱情观:
“爱便爱,不爱便丢开。”
当萧红追问丢不开怎么办的时候,他爽朗地回答:
“丢不开,便任他丢不开。”
爱情观的失衡,为两萧的悲剧埋下了隐患。
 逃出东兴顺旅馆,生下孩子,没钱滞留在医院------种种困难的日子里,都是萧军陪伴在侧。
逃出东兴顺旅馆,生下孩子,没钱滞留在医院------种种困难的日子里,都是萧军陪伴在侧。当两人凭借小说在上海小有名气,生活得到改善后,两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。
首先是因为萧军的风流,他与多名女子保持着暧昧的关系。
这让萧红苦不堪言。
其次是因为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与莫名其妙的自尊心。
在文学成就上,萧军自认为高出萧红。可是,身边的朋友都认为萧红是天赋型作家,而萧军是努力型的。
在天赋面前,努力一文不值。
这深深刺痛了萧军,也是两人爆发激烈矛盾的根源。
最关键的是因为萧红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在最潦倒的时候,萧红是完全依赖着萧军,萧军则非常享受这种依赖。
当萧红的作品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,她强烈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。
她不满足依附萧军,而是要开辟出自己的文学道路,两人时常爆发激烈的争吵,萧军甚至会动手。
萧红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抒发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苦闷心境:
“往日的爱人,为我遮蔽暴风雨,而今他变成暴风雨!让我怎来抵抗?敌人的攻击,爱人的伤悼。”
尽管彼此带给对方伤害,但是萧红仍然是深爱着萧军。
但是,萧军已经做好的离开的打算。
他的决定完全符合他的爱情观——不爱便丢开。
萧军对萧红事无巨细的关心非常厌烦,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去延安,去打游击战。
而萧红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写作。
巨大的差异摆在面前,萧红痛下决心,选择离开。

萧红与萧军的这段关系,是一个女人的不断成熟的过程。
女人总是在爱情中慢慢学会了成长。
她从一个只知道躲在旅馆里写作怡情的少女,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人。
不幸的是,她的成长并不能被爱人所接受。
这段在外人看来非常匹配的恋情就这样黯然谢幕了。

与萧军分开后,萧红迅速地与端木蕻良确定了关系。
时间之仓促,让周围的朋友们都质疑这段关系。
萧红与端木结婚的时候,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。
她想到了流产,奈何月份太大,危险程度太高,只好作罢。
端木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情况,这才得以顺利结婚。
端木蕻良与萧军都是东北人,但两人的性情截然不同。
萧军豪爽坚毅,而端木性情软弱多疑。
萧红在上一段感情里,一直处于弱势被保护的地位。
这令她非常不满。
可是,在与端木的关系中,她得到了自尊心的强烈满足。
端木欣赏她,尊重她,承认她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。
她与端木的关系,成了她与萧军关系的倒置。
端木成了被保护者,萧红则是保护者。
刚开始,萧红确实享受这种“高高在上”,受人敬仰的感觉。
时间一长,她就开始受到了反噬。
战争开始了,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逃难。
在朋友的帮助下,萧红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船票。
但是,第二天出现在码头上的却是端木。
这也是端木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地方:他怎么能抛下大着肚子的萧红独自离开?
萧红只能再次等待救助。
就像她后来向朋友诉苦:
“我总是一个人走路,以前在东北,到了上海去东京,现在到重庆,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。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------”
在重庆,萧红与端木重逢。萧红生下孩子,可是孩子在三天后死去。
萧红没有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悲伤,这不禁让人怀疑孩子的死因,是否是一个母亲的残忍。
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带着孩子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。
萧红与端木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。
可是,这段生活却让萧红更加疲惫。
友人曾经回忆,大腹便便的萧红在逃难的人群中,自己撑着伞,提着笨重的行李,举步维艰。
而轻装的端木,则拿着手杖站在一边。
萧红又回到了被男性支配的宿命中了。
而且端木一直在朋友面前否认自己与萧红的婚姻关系。
萧红一面要创作,一面还要照顾端木的饮食起居,甚至还会帮他代写文章。
长年的劳累加上本身体质弱,萧红在1938年就开始出现肺病的症状。
为了治病,萧红与端木逃到了香港。
不久,战火就燃烧到香港。
端木四处奔走,有时也只能留萧红一人。
幸好,萧红弟弟的朋骆洛宾基联系到他们。
在萧红重病期间,一直都是骆宾基陪伴左右。萧红一直担心端木会不告而别,留她一人。
她实在是无法忍受在异乡孤独凄惨地死去。
最终,端木还是没有走成。
在治病的期间,两人的矛盾越发地尖锐。
萧红认为端木只听医生的,不考虑她的感受。
这时,她想到了萧军,并且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打个电报给萧军,萧军肯定会奋不顾身地来接她。
从这里不难看出,萧红对萧军还是充满着依恋的。那段甘苦与共的岁月,扎根在记忆最深处,是无法改变的。

从骆宾基的回忆文章里,萧红不止一次地后悔与端木地草率婚姻。
那段婚姻更像是一种疗伤,一种逃避,而不是爱。
正如萧红自己说的:
“萧军的离开时一个问题的结束,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。”
骆宾基曾经问萧红,为什么能和端木这样的人生活三四年之久。
萧红无奈地说:
“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,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。”
和萧军的分开,是筋骨之痛;与端木的结合,只是皮肉之伤。
弥留之际的萧红,不停地叮嘱端木一定要在她死后,将她安葬在鲁迅的墓地旁边。
她说“半生尽遭冷遇白眼”,只有在上海与鲁迅相处的日子里,让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鲁迅先生就是萧红童年时期的祖父:慈爱、温暖、包容、善良。
漂泊半生的萧红在香港去世,由于乱世,端木还是没有满足她葬于鲁迅身旁的遗愿。
在男性世界里,萧红受尽了各种折磨:物质上的,情感上的,身体上的------
她没有退缩,没有消沉,在她31年的短暂生命里,用血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炙热作品,鼓舞着后世女性勇敢向前。
“她以一己病弱的血肉之躯,承担了女性民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。”
